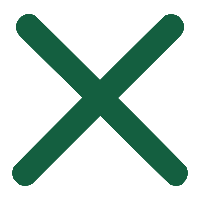(余婷报道)从住院楼22层医生办公室的玻璃窗向外望去,天空低沉,医院南大门主干道北京东路的汽车仍然川流不息。
雨夜让病房显得比往日更安静些,偶尔传来监护仪滴滴的声响。走廊的尽头是个单间,45床,老林。老林已经在这住院快一个月了,胰腺粘液腺癌多发转移,胸腹水,肠梗阻。
他不是我经管的病人,但因为他起初到病房一米八多的大高个,从我身旁走过时让我印象深刻,再后来是大查房时,我发现他的病床旁尽是鲜花绿植,比如绣球、月季、红掌之类。
他的胸腹水与常见的不一样,特别的粘稠,似胶冻一般,无法自行从引流管中流出,只能拿注射器一管一管的往外抽,值班时帮忙抽过一回。每天一两千毫升的腹水抽出后,也只能略微缓解一点点他的腹胀。因为腹腔转移的原因,他还合并了肠梗阻,圆圆的肚子一叩诊尽是鼓音,他已经半个多月滴米未进了,全靠肠外营养,屁也没放一个。
轮到我值下一个晚班见他时,他已经完全起不来床了,身上插着胃肠减压管、导尿管、胸引管、腹引管、中心静脉置管,胸前还贴着电极片绑着心电监护仪,这两天开始说是有些嗜睡了,血压也开始下降,靠多巴胺泵维持着。整理完病历接近晚上11点,我想溜一圈病房再回值班房躺躺。走到45床门口发现灯还开着,于是打算进去看一下监护仪上的数值,从门口的玻璃窗往里看。
“林老,这是病房,怎么能抽烟呢?”老林没有理会我的话,用颤颤巍巍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那支刚点燃的香烟,递向了自己的嘴边,深深地吸了一口,他本来就凹陷的双颊更明显了,然后白色的烟雾从口腔和鼻子冒出,眼神空洞的望着我,用微弱的声音说:“我好难受好难受,我……想抽一支烟,抽支烟就能舒服一点。”我被噎住了,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,只能将语气放柔一些,“可是这是病房,你生病了,按规矩来说不能抽烟,知道么?”“我知道,我抽了五十多年的烟了,我知道我的病,再抽不了两天了。”
他黑黑柴柴的手夹着烟定在半空中,前端的烟灰就这样掉了下来落上他的身上,我赶紧去帮忙掸掉以免烫到他。“那,破个规矩,再吸一口就灭了吧。”
我取过他指间的烟,递到他嘴边。老林再吸了一口吐着烟圈说:“谢谢,你太好了,太好了。”家属在一旁拉着老林的手红着眼圈说:“你看,大家对你多好,本来是不行的,只要你舒服就好,只要你舒服就好。”
掐灭了烟头后,我握住老林的大手说:“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没力气,特别特别的沉,身上压了千斤重一般?”“你太了解我现在的感受了。”“害怕(死亡)么?”“我不害怕,我只希望这一天快点。”我也忍不住红了眼眶,“好,谢谢,谢谢,我要睡了……”老林查拉的眼皮闭了闭。
我走出病房轻轻带上房门,看着手中那掐灭的半支烟,突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肿瘤大夫,为晚期病人所做的,似乎还不如这最后半支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