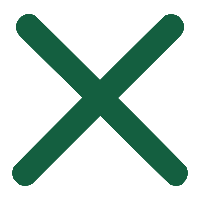(李倩倩报道)护士站奶白色的瓷瓶里,几枝素白的瓷莲正托着浅黄的花蕊,阳光落在釉面晕出温润的柔光,像把半盏春阳揉进了瓷里。望着这瓶瓷器花,我的思绪忽然穿过山高水长的距离,落进了意大利尼瓜尔达医院肿瘤科那间飘着消毒水气息的病房,落进了那个裹着浅金色阳光的下午。
71岁的罗伯特,是我在尼瓜尔达医院遇见的一个患者。他因多发性骨髓瘤伴骨病及贫血入院,我第一次推开他病房门的时候,他正半靠在枕头上,脸朝着窗户的方向,整个人缩在米白色的病号服里,像一片被风吹得打卷的落叶。之后的每一次查房,我总能撞见他沉默的侧脸,下颌线绷得很紧,眼窝因为贫血陷得很深,连落在他发顶的阳光,都像是蒙了一层薄纱,暖不进他的神色里。
作为科室里的亚洲面孔,我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时,他原本垂着的眼睫猛地抬了起来,浅褐色的眼睛里翻涌着不加掩饰的惊讶。他转头看向我的带教老师Edou,语速很快地说了一串意大利语,Edou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,对着罗伯特介绍:“这是来自中国研学的护理人员,她叫倩倩。”罗伯特的眼睛里很快漫开温和的笑意,他对着我抬了抬手,开口时是意外流利的英语,在此之前我接触的几个患者都只会说意大利语,每一次交流都要Edou在中间连比带划地翻译,憋得我常常有满肚子的话卡在喉咙里。听见他的英语,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往前迈了半步,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,连带着声音里都沾了点雀跃的温度。
那天我们聊了很久,我终于把之前几次查房攒下的疑问问了出来:“您的脸色看起来总是不太好,是不是身体很不舒服?”他的指尖轻轻按在自己的腰侧,那里是骨髓瘤骨病最常发作的位置,“骨髓瘤破坏了骨头,贫血又让我没力气,连翻个身都要靠这个。”他指了指床边的手拉辅助器,骨节分明的手指因为用力泛着青白,说话的间隙里,还会忍不住闷哼一声,是骨痛发作时的隐忍。我下意识地想去扶他的手,他却对着我摆了摆手,浅褐色的眼睛里蒙着一层化不开的无奈:“已经这样很久了,习惯了。”那是我第一次读懂,被疾病困住的人,连“求助”都会变成一种小心翼翼的退让。
之后的好些天,我总是找机会往他的病房跑,哪怕只是帮他把滑到肩膀的被子拉好,或是把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水杯递到手里。直到那天跟着Edou做完一组治疗,我路过他的病房时,看见他正半靠着枕头坐着,阳光落在他的银发上,像撒了一层碎银。我推开门,没等他说话先开了口:“今天的阳光很好,您感觉怎么样?”他的眼睛亮了亮,问出了藏了很久的问题:“你来自中国的哪里?”“江西南昌。”我回答。他皱了皱眉,显然没听过这个名字,于是我掏出手机打开谷歌地图,指着中国东南方那片被青山绿水裹着的城市给他看。他凑过来盯着屏幕看了很久,之后对着我抱歉地笑:“中国太大了,我知道的太少,只听说过北京、上海、香港,还去过台湾,那是个很美的地方,我一直很向往中国。”
于是那天的病房里,消毒水的味道慢慢被细碎的暖意冲淡。我给他讲赣江的水,讲滕王阁飞翘的檐角,讲瓷都景德镇里,匠人捏在手里的瓷泥会在窑火里开出花;我翻出手机里的照片,给他看科室里的大合照,他指尖隔着屏幕一个个划过照片上的人,看到护士万树芳时,他忽然顿住了,指尖点在屏幕上,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赞叹:“她的眼睛像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月光,温柔又明亮。” 看到站在合影中间的院长时,他又笑了,对着我挤了挤眼睛:“这是你们的BOSS,我认得这种‘领导人的气场’。”
他也开始跟我讲起了他的生活:他的妻子在米兰开了一家小小的面包店,每天下午四点会带着刚烤好的可颂来病房,面包香能飘半条走廊;他的女儿已经工作了,是一名律师,“她很厉害,能帮很多人解决麻烦”,说起女儿时,他的眼睛里会亮起星星,连带着脸色都多了几分血色,他枕头边的靠垫上,印着一张女儿的照片,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两颗小虎牙。“她总说要带我去看世界,可我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。”有一次他摸着靠垫上的照片,声音轻得像叹息。我走到他的床边,告诉他:“我每天都会来,只要你想聊天。”
康复科的同事来帮他做功能训练的那天,我守在病房的门口。我看见他攥着辅助器的指节泛着青白,额角的汗滴砸在地板上,晕开小小的湿痕。当他终于借着辅助器的力量,把身体从床上撑起来,双脚轻轻碰到地面的那一刻,病房里忽然静了下来,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。然后他慢慢转过身子,看向窗外的天空,忽然捂住脸哭了起来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,不是因为骨病的疼痛,不是因为住院的孤单,是一种攒了太久的、终于破土而出的喜悦。他哭着说:“我以为我再也站不起来了,以为自己只能像个废人一样躺在床上。”我走到他身边,轻轻拍着他的后背,像哄着一个难过的孩子:“你看,你做到了,只要你愿意往前走,就没有人能把你困在原地。”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,眼睛通红,却笑着点了点头。
离开尼瓜尔达医院的前一天,我拿着那只从景德镇带来的瓷瓶走进他的病房。米白色的釉面,瓶身上描着浅淡的青花莲纹,瓶里插着我从行李箱里带来的瓷莲,是出发前,景德镇的老匠人送给我的,说 “带着它,就带着家乡的温度”。看见我手里的瓷瓶,他先是愣了愣,之后慢慢伸出手,指尖摸着瓷瓶的釉面,指腹蹭过青花的纹路,语气里带着不敢置信的温柔:“这是给我的?”“是从中国景德镇带来的,” 我把瓷瓶放在他的床头柜上,阳光落在瓶身上,泛着温润的光,“瓷瓶是景德镇的泥烧的,瓷花是景德镇的手捏的,带着中国的温度,也带着我的心意,希望它能陪着您。”他攥着我的手,粗糙的掌心带着薄茧,力气很大,“谢谢你,来自中国的小姑娘,你给我的,不只是一只瓷瓶,是我这大半年里,最暖的光。”我看着他浅褐色的眼睛,里面映着瓷瓶的光,映着窗外的蓝天,我告诉他:“在中国,我们总说‘瓷有韵,人有情’,不管在哪里,好的心意,都能暖到人心里。”
护士站的瓷瓶里,瓷莲还静静开着,风从窗外吹进来,带着冬天里浅淡的暖意。我想起罗伯特的笑,想起他攥着辅助器站起来的样子,想起那只漂过半个欧洲的瓷瓶,原来护理从来都不是语言能阻隔的东西,是藏在一杯温水里的温度,是耐心的陪伴,是一只带着家乡温度的瓷瓶,是不同肤色的人,心里都藏着的,对温暖的渴望。而那只瓷瓶里装着的,从来都不是花,是跨越了山海的善意,是中国护士藏在细节里的温柔,是两个国家的人,对着彼此伸出的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