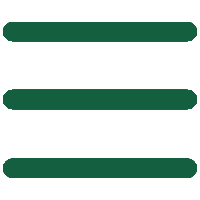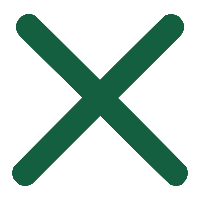“凡大医治病,必当安神定志,无欲无求,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,不得问其贵贱贫富,长幼妍蚩,怨亲善友,华夷愚智,普同一等,皆如至亲之想。”这是孙思邈的《大医精诚》的句子。长大后常听母亲说,在和父亲恋爱的那几年里,父亲喜欢把这篇文章念诵给她。两人靠在河畔,微风轻拂,望着远方的鄱阳湖,时光如水般流过。这成为母亲心中最美的记忆,也播种下了我从医道路的最初种子。
父亲是中医,当年是小邹,历任邹主任、邹院长,如今实实在在成为了老邹。这些年来,老邹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,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指路明灯。父亲从小山村起步,走到镇里、县里,后来又走进市里,成为了江西省名中医。一步步,父亲走的艰辛,但却异常坚实。犹记得少年时,家里的庆祝活动父亲长期缺席,难得的家庭聚会也经常会被一通电话打断,然后他就急匆匆赶回医院。父亲一生节俭,但却是最早买手机的那一批人,自此拥有了手机后,外公的七十大寿、我和妹妹的十岁生日、中秋夜、除夕夜,只要那个小小的塑料盒子发出刺耳的铃声,父亲就要跟我们说再见,然后回到他的岗位。所以少年时的我,对父爱的认知是很模糊的,妹妹甚至曾经在作文里写下过“我的爸爸不爱我”这样的句子。
辛勤的工作带来的是令人惊叹的好口碑,最让我自豪的就是父亲办公室挂着层层叠叠的锦旗,金灿灿红艳艳,而且每年都要更新一批,历经数十年下来可能几百面之多。父亲说,行医一方黎民,造福一方百姓,乡里人淳朴,你真心帮助过他们,他们就喜欢用最朴素的方式感谢你。
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10余年,终于让我义无返顾地走进了医学院,与父亲不同的是,我走进了西医的院校。我没想到医学教材居然那么多那么厚,厚到全部叠起来可以顶到一个成年人的下巴。记忆力并不好又年少顽劣的我,差点把这些书扔进了学校后的池塘。父亲得知后并没有怪我,只是那年暑假,他让我把他读过的所有中医教材、经典、方剂学一本本摞起来,直到超过了我的身高。然后再一本本的塞回去,一边塞一边说:“医生也是一门手艺,手艺不精是要被人砸饭碗的;你学西医更加如此,现在还是基础,知识不断更新,你要学一辈子。”走进临床后,我身体内那个被父亲植入的医生灵魂终于被按下了扳机。在一个个病例指导下,我开始真正热爱这门学科,期待每一次的课程,期待着自己职业生涯开启的那一天。
如今父亲已年逾花甲,但仍在每日勤勉工作。从他身上,我懂得了努力和奋斗的真正含义,也懂得了这一身白衣所承载的重量。我也开始习惯加班,习惯在任何时候只要接到病房的电话,都要第一时间回到工作岗位。我也会不断学习,更新知识,做个好“手艺人”。我相信无论在哪里起步,在我们这个和平的年代,只要一直认真努力,就一定能收获满满的成绩和感动。
2020年春,新冠疫情爆发。疫情爆发伊始,父亲作为九江地区的抗疫专家组成员,便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,四处奔波。大年三十晚上,父子围炉夜话,父亲说:“儿子,抗日战争时期,太行山区有句话叫“母亲送儿打东洋,妻子送郎上战场”,你是呼吸科医生,这场疫情,如果国家需要你,你应该要冲到第一线去,这是你的责任。”一席话说完,我看到的是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样子。医之大者,为国为民,于是当驰援湖北的命令来临,我主动请缨出征,光荣的成为了江西省援鄂第一批医疗队员,走向战场,奔赴武汉。在艰苦卓绝的54天工作后,迎来了武汉疫情的关键性胜利。这一刻,我感觉我接过了父亲递过来的接力棒,真正成为了这个伟大国家一名合格的医生,和我的战友们、同事们,和我们几百上千万同行们一起扛起了整个中国。
这就是我和我的父亲的故事。我很幸福出生在传统的医学家庭,并得到了父亲的不断引领。我的从医生涯,闪耀着前辈们的人性光辉。正是有了一辈又一辈的传承,我们的医学事业才如此生生不息,枝繁叶茂,也才能守护我们千年的祖国不被疫病所击倒,还百姓安宁。
邹俊韬,江西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主治医师、江西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
邹必英,九江市中医医院肝病科主任、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